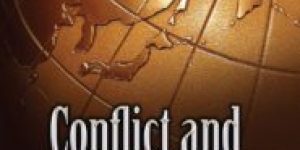我的故事 ~ 10. 一个人的党
No comments yet1998年,珀斯,朋友聚会。
珀斯中国领事馆首任总领事要回国了,谈论中都有些舍不得。总领事颇具亲民之风,给人的印象是几乎跟每个华人都熟悉。但凡做人做戏做官,玩股票玩收藏玩政治,到了这种让人惦念的份上就是人尖儿了,那年还是一个澳大利亚全国大选年。谁说华人对政治不感兴趣?我认识的圈子对投票还是上心的。甭管选谁,投票日必到场。澳洲的规矩,不投票是要罚款的。虽说不多,没挣着的钱咱不奢望。可进了口袋的银子,没必要再拿出来吧?
聚会结束驾车回家,无意中听到ABC电台采访,一个叫Ed 的华人要成立一个政党参加大选。当时采访就在他家,后院立了抗议种族主义的标语牌。他说当初买地盖房时,因为他一张亚洲面孔,每天都有人往院子扔石头、砸东西。报警察也不管。知道是谁干的,但警察说法律上要抓现行才行,捉贼捉赃,懂不懂?一整年的骚扰,害怕得不行,烦得不行,可遭罪了。所以下决心把党建起来,提高华人声音。这人真够胆儿。不说古往今来,这就是澳洲历史上没有过的事儿,爷们儿!血性!有机会一定要拜见一下高人。见不着咱也投他一票!不曾想才没过两天,有人就介绍我认识了Ed 。
见面是在Ed 家,不少人呢。一番寒暄,才发现珀斯各大学的讲师教授就有好几位,中国的、东南亚华人、 印度的都有。我后来发现,这些人一个个都是智囊。Ed即黄先生。这天大家来是要讨论成立团结党参加全国大选的事儿。黄先生的名言是“一个人说话没人听,一个党说话就有人听了。”从此我无意中卷入一场政治选举,见证了澳洲历史上最大的华人参政潮。
那年澳洲政坛出了一件邪乎事儿。
一个新当选的联邦众议院议员汉森公开发表反亚裔,反土著和反移民言论。一时间成了某些极右翼者眼中的英雄。汉森小人得志成立了“一族党”。叫嚣要亚洲人滚出去。更猖狂的甚至要土著人“滚回他们来的地方”。这澳洲大陆本来就是人家土著人的,该谁滚呀?为了拉选票,一族党公布所谓“零移民”方案,主张将所有在澳洲的各种难民五年内全部遣返回国,并呼吁政府取消多元文化政策,强制移民英语考试,严格控制移民年迈双亲入境。霍华德执政的自由党对一族党态度暧昧,基本上不反对,因为汉森原来就是自由党分化出来的右翼分子。一族党的猖獗成了华人参政的主要原因。应了那句俗话:兔子急了也踹鹰。东部的悉尼有个侨领率先成立了一个政党,取名团结党。黄先生与东部取得联系,决定也成立西澳的团结党,参加当年竞选。
这黄先生原来经营一个邮局代理多年,夫妻店,认识不少人。最近刚退休,将店卖了。他当过多年邮政行业的协会主席,代表行业进行过各种谈判。比如争取公平竞争环境,跟政府讨价还价等等,积累了不少“参政”经验。黄先生说成立一个政党参选需要两个基本条件。首先要有党章 (constitution),东部的团结党已经有了,拿来改改就行。其次起码要有500个党员,这也不难。关键的是要提名候选人,分参议院候选人和众议院候选人。
首先是参议院(the Senate)候选人。当时统计珀斯华人不多,所以光华人不行,还要联系其他亚裔组织,土著更是盟友。一番讨论,四方联系,提名的是Ted Wilkes 。他是土著人,当选过年度人物,有代表性,也有号召力。团结党只要拿到4%的选票,就可以有一名参议院议员,任期六年。
接下来是众议院(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候选人。团结党作为小党没法在每个选区都提名候选人。所以作为选举策略,只能找那些两大党选票接近,势均力敌的选区。有时候选举只差几千票,甚至几百票,这时候小党的原始票就管用了,给谁谁赢,几百票的差异就可以决定胜负。秤砣虽小压千斤。不过政府公职人员不能当候选人。大学的这些智囊都没戏。辞职去竞选?万一选不上不是砸了自己的饭碗吗?这年头找份工作不容易。不少人还是刚从学位、工作和身份的三座大山下解放出来的。所以黄先生当仁不让是团结党候选人, 印象中有一位大学老师的妻子,香港人,干餐馆的;一位娶了中国老婆的白人,二人开杂货店的; 还有一位医生。
最后是钱的问题。提名候选人要给选举委员会交提名费,众议院和参议院不同,每个人几百上千不等。几个选区候选人提名下来就是一大笔钱。 团结党没钱。后来东凑西凑,自筹捐款等等,总算给候选人筹足了提名费, 竞选就正式上了议事日程。
开会基本上都在黄先生家。两层小楼就老俩口。孩子们都长大了离家自住,所以相当的宽敞。黄太太是厨艺高手。每次会议开完后都会在他家大吃一顿。一张大圆桌面,就像在餐厅那样,加在餐桌上,变成更大的一张桌子,满满一桌香喷喷的家常菜,非常丰盛。 一看就知道这是经常聚会的地方。如果有人称赞某道菜,黄太太便立马开免费教学班,你不学会下次都不好意思来。当然偶尔也在别的家开过。有一个高级讲师的家,从客厅到厨房,都是贴墙而上的书,没有书架。各种书承当了墙纸的功能, 倒也别具一格。会后也是大吃一顿。
团结党成立后第一次大会在一个社区中心举行。来了近百人。大多亚洲面孔。黄先生和黄太太夫妻忙前忙后。他们就是那种典型的夫唱妇随几十年磨合非常默契的老夫妻。当时选举了主席,党中央成员等等,都是按程序走的。我理解这就是党员大会了,就是南湖红船那种。
团结党的出现让两大党感到力量和威慑。这种选举阵势真的让执政的自由党着急了。华人的参政让他们看到华人并不是主流社会臆想的那样只会在餐馆炒菜,逼急了也会反抗。所以大选前就有许多大党跟小党的讨价还价,种种选票交换的谈判。有时大党发现小党的候选人不错,便召至麾下。而候选人临阵变换阵营也是常有的事。春秋无义战。孔夫子鲁国人,可祖籍宋国,还拿过卫国的俸禄呢。圣贤如斯,也不怪后人。
团结党有时也被请去参加各党的种种互动。一次我被派遣去参加一个早餐会。不巧车坏了,只好去赶凌晨5点50 发车的第一趟公共汽车。记得是7 月份,正是澳洲的“数九寒冬”。早起还冻手,天是黑的。心想快点上车找个座位。车到了才发现是满的。几乎清一色的工人,有的身背工具袋,有的手提工具箱。 我找个扶手站着,旁边是一个高大的中年男人,身上的浅棕色咔叽工装印有一家建筑公司名字。我想让自己站得舒服些, 移动中不小心踩了他一脚。没等我开口这人先说了:“对不起,我的脚太长了。”这哥儿们真逗。我们聊了起来。他是一个工地的工头,旁边一身蓝的是建筑工地的保安,他朋友。
“今年大选真热闹。谁会赢?”我问。
“不到开票的时候谁都不知道。如果猜得着还不如去买彩票。”挥之不去的幽默。
“我不会去投票。”蓝衣服插嘴说,“去他的大选,新魔鬼老魔鬼都一样……罚款?罚款也不投。”
下了车时天还没亮。高一脚低一脚紧赶慢赶还是迟到了。讲话的是一个候选人。记不清说了些什么。早餐非常简单,三片说不上名的小点心,倒也精致。早餐会7点开始8点结束,西装革履的人们夹着公文包各自赶着9点上班去了。我是澳洲政治文盲,但第一次感到了两大党的区别。这些人不会去挤第一趟公共汽车。 我在车上遇到的人也不会参加这样的早餐会。
华人的身份认同让我一直跟着参加团结党的活动。不是主要的决策人物却努力保持跟中央一致。选举要造势。没钱登广告。黄先生叫写文章。我便找到珀斯历史上第一份中文报纸《西澳华文报》在头版登了我们的文章:
“……报载澳大利亚的主流社会对汉森及其一族党并不反感。此说并非空穴来风。昆士兰州议会选举,一族党出尽风头。一些人说汉森反移民不对,但是她对土著的批评没错。 可见白澳幽灵犹在。友人云,汉森不足虑,她只是个酒幌,可虑的是背后抄刀的智囊及日成气候的一族党。此言甚善。澳大利亚是个民主国家,说说无妨。但若让利益相违者操了你的生杀大权, 你便成了笼中鸟,网中鱼。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龙卧浅滩,奈何奈何?因此,要紧的是要看好你手中的选票, 不要丢了,不要忘了,更重要的是,不要填错了。”
填选票绝对是个技术活。两张选票:一张选人、一张选党。参选的候选人有几十名,党也有十几个。没多少人能弄明白。即使对选举不在乎的人,随便填,不小心画错了成了废票,冤枉跑一趟不是?要命的是各候选人都花了银子,所以都怕选民填错银子进了别人口袋。 于是各党“投票指南”应运而生。
10 月 3 号投票日,我家对门小学是个投票点。那天小学外路旁早早就树立起了各党候选人的广告牌,花花绿绿大头照。各党义工每隔三五步,夹道欢迎般地迎接选民, 递上本党投票指南。我领了差,前去为团结党当义工。好位置都被大党占了,他们人多。我在一个拐角处,身旁是几叠裁成两个巴掌大小的填表指南。斜对过就是一族党的一个老头。别人拼不过,还能输给他?团结党没钱可人气不能输, 我心想。陆陆续续有人来了。有的选民主意已定,只接自己心仪的候选人投票指南。更多的选民,不知道是出于礼貌还是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政治倾向,对递到手边的全部照单全收。我也见人就递上,总之要抢在一族党的老头之前。很快我就发现发得太快,材料剩下不多,于是就只递给亚裔面孔的人。即使这样,中午刚刚过了就快发完了。 黄先生过来,我向他报告。于是又叫报社加印。
全国选举结果当晚就出来了。团结党在众议院无人当选。东西部皆完败。在参议院获得93,968张选票,占0.83%,还不到全部选票的百分之一。而一族党选票过百万,占9%,得到一席参议员。在其重镇昆士兰州获得全部89席中的11席位。
澳洲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华人参政潮轰轰烈烈地以失败告终。选举虽败犹荣。一族党好景不长。汉森像个明星似的到处演讲,因为乱花纳税人的钱当了被告。因此被后来当了澳洲总理的阿博特清理门户,弄了下去。连选议员没成而渐渐淡出政坛。一族党腐败内斗等丑闻不断被媒体曝光,从此一蹶不振,再没起来。当然澳洲的政治生态也无法容忍极右势力。
没有了对手,团结党也淡出了。智囊们纷纷回归大学,各干各的。事情到这儿也算完了吧?没呢。黄先生仍坚持在团结党抗议种族主义,替华人社区发声。那段时间我每天都能收到他群发的邮件,大多是他写给政府各机构、党派、 媒体的信件。比如一位C先生,中学数学老师。因为拍了一下女学生的屁股被家长告到学校说是性骚扰,被教育局停职。一直在上诉,认为该家长种族歧视,不愿意让亚洲人教其孩子。黄先生用团结党主席的名义写信支持他上诉。
还有一件让黄先生特别气愤的事,后来闹上了媒体。埃迪斯科文大学的一位华人讲师,刚从德国受聘到珀斯不久,住在城里的公寓。 1999年中国除夕之夜,该仁兄不知今夕是何年,在家一直工作到夜里12点,腹中饥饿,下楼想买些吃的, 不料被不知哪儿来的两个警察抓住。他本能的挣扎,想问明白什么事儿,谁知越说话越麻烦。警察根本不理会,最后是拳打脚踢按倒在地,拷上手铐扔进警车,直接拉到警察局。第二天审问时警方才意识到,这个被关了一个晚上,满身伤痕,能说一口流利英语、汉语和德语的28 岁年轻人,不是他们要找的毒贩, 抓错人了!黄先生后来跟警方杠上了。这不就是洛杉矶罗德尼•金案的珀斯翻版吗?他同样以团结党主席的名义强烈要求警方不能简单道歉赔偿了事。应该起诉当事警察的“种族主义”罪。他一直坚持到两个警察受审,受到处罚才罢休。
我后来还参加过好几次一年一届的党员大会。最后一次只有不到十人,便也退出了。与黄先生便少有联系,只是不时在一些活动上看到他和黄太太的身影,寒暄几句。不过我知道他后来成立了“山东同乡会”,当会长,帮助很多457 短期劳务签证的人,为他们争取政府保障福利,为此大选期间还跟托尼 • 阿博特讨价还价。
黄先生是山东人。16岁离家投奔香港的舅舅当学徒。虽是亲戚,却也寄人篱下,总不如家里爹疼娘爱。表姐在悉尼念书,当年假期回来,一番聊天,结果就是黄先生拿到了澳洲的“科伦坡计划奖学金”(Colombo Plan) ,于1954年来到澳洲念中专,学农。怎么样? 是不是跟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们这些拿奖学金出国的人有些像?虽然早了30多年。人的命运就是这样。话说这天下掉馅饼的事也真有。您还别不信!拿过这“科伦坡计划奖学金”还有什么尼泊尔的前总理,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部长, 印度的著名医生……不少是世界名人。但是当时像他这样毫无家庭背景,只靠奖学金的华人在澳大利亚真是凤毛麟角。而在白澳政策的时代,他的亚洲面孔可遭了老罪, 受尽白眼。这让他一生都痛恨种族主义。
白驹过隙,仓海桑田。到了2014年。一转眼离团结党成立过去了16年。无意中我惊讶地发现团结党的网站还在运作,还加了推特群, 不可思议。于是一天下午,坐在黄先生的客厅,我们聊了起来。
黄先生还是那样硬朗,似乎看不到岁月痕迹。“ ……对,团结党还在。只要有6个人就能保留注册。有章程就可以运作。只是不能参加竞选。”
我好奇的是,一个人的党,16年, 为什么?
“因为我喜欢政治。对某些人来说,政治是最肮脏的游戏,但它是最有效的改变社会的方法。……为什么我会对政治感兴趣? 这来自我个人的经验。50 多年前,我妻子要到澳洲跟我团聚,从山东到香港, 等澳洲配偶签证,路上走了三年。在香港呆了很久。我每天盼,每个星期都去问,没有结果。不知怎么办?后来一个人对我说去找议会的议员。我连这个人的名字都忘了。真管用。三个月后她就得到了签证。这个人改变了我,完全改变了。一辈子我都记得他。政治权力决定一切。我喜欢政治,就是要帮助其他人不要陷入与我同样的经历。至少我可以帮助他们。……我现在退休十几年了。所有的工作都是义务的。你说我活跃?对,一分钱没有但是我乐意。我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十年吗?二十年吗?因为我喜欢政治,我会在政治中直到我死去……。” 黄先生说起来就滔滔不绝:
“你现在每天都做些什么呢?”
“我的日程是这样的。吃完早饭,先检查所有的电子邮件,然后浏览一下报纸。大概花上 3 个小时。然后午饭午休。会客见朋友都是下午。你以后来也最好下午来。上午我要工作。电子邮件世界各国都有。报纸只是浏览,什么都看。两份中国的,像新华社报道等,一份香港的、一份台湾的、一份新加坡的,两份日本的,然后就是BBC、《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还有澳洲本地的《悉尼先驱晨报》、《澳大利人报》、《西澳大利人报》和本地的小报。一共多少,让我们数数它,14份。所以我每一天都会浏览这 14 个网站。当然都是英文的。你知道报纸就是一切,全世界新闻都知道。我不仅读政治新闻,什么新闻都读。有意思的就拷贝下来, 群发出去, 请他们评论或回答。今天针对安倍,明天给奥巴马,后天给阿博特……我也给中国的温家宝总理写过信。我的群发有好几百人。包括欧洲国家的领导人、亚洲领导人,还有世界各种报刊杂志的编辑。有时我写些评论,有时是征求他们的意见,想谈谈吗?给他们一个机会。经常是什么答复都没有。不过有些人会定期送一些信息来。”
“没回答你还发送?”我问。
黄先生继续道:“我的目的是要传递消息,是否回答不是我考虑的。人们有不同的看法,但对我来说答不答复没有什么。你不喜欢可以删除。《纽约时报》总是自动回答,说明他们收到了,但不发表评论。我有时使用团结党的名义,大约一半用笔名。我有十几个笔名, 就是不想让人知道是否中国或日本或欧洲人。这也是一种享受和一点乐趣,正确吗? 保持我的大脑清醒。因为退休了要有爱好。碰巧的是我喜欢政治。我可以使用计算机作为一种工具来传播信息。不断地连接与外面的世界。
“你真的从来都没收过回信吗?”
黄先生笑了:“有一次奥巴马竞选时给我回了个邮件,当然是给团结党的,要10 美元捐款什么的。他想要我转发给别人给他捐美元。 我回信说如果你保证不在亚洲开战,我的10 美元你是肯定可以拿到手的。不过有人说是这个信件是假的,网上要钱都是骗子。“
我说:“您把奥巴马的信转发给我看看,行吗?“
“没问题,我这辈子做过很多工作,几乎各州都呆过,但都是在乡镇。做邮局代理才来珀斯。那时钱不多,一共干了16年,勉强攒钱够孩子的教育费。就退休了。”
“你喜欢澳洲吗?你觉得自己是澳洲人吗?”我问。
“我在澳洲住了 60 年,我喜欢澳大利亚。我是澳洲人,但我也是中国人。我不能否认这一点。我一样爱我的家乡。那是我出生的地方。虽然我只呆了16 年。你知道,抚养你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永远不会离开你。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仍然是我的故乡。如果我死了,我的坟墓是在中国,父母在的地方才是家。虽然我的父母是在坟墓里,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这60 年来几乎没有改变我。因为对我来说。澳洲仍然是一个外国的国家。我仍然认为去中国是回家,是我的家。……我喜欢多年前在波特兰港口的时候。货船到达的时候,有来自中国或台湾的运盐船。他们很惊喜地发现有中国人,请我们去船上,很开心。然后我们也带中国船长和船员逛逛。作为回报,他们请我们上船吃饭。我喜欢在波特兰的工作。虽然只有两年。但是可以常常看到来自家乡的人……”
我的思绪像风一样飘起来。 黄先生的声音渐渐远去,就像在梦里……我也上过中国的南极考察船《极地》和《雪龙》号。 船长和船员请我们上船参观,我们带他们在珀斯逛逛。然后在船上吃一顿。船上的蒸馒头永远难忘。只有家乡才有的味道!那时候,大街上见到一个中国面孔就上去搭讪,就像赶集遇到亲戚似的……我们的经历何其相似乃尔。
离开黄先生的家,我将奥巴马的信件转发给大学的一个IT教授。猜猜?那地址是真实的。
You May Also Like
Comments
Leave a Reply